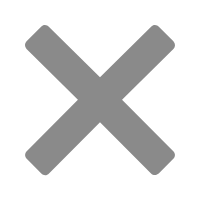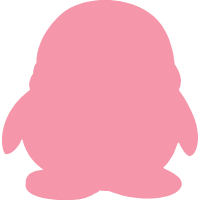2
真好听,像戏文里那些个儿公子哥儿的名儿。
「周公子。」我学着许家阿妹的样子行了个礼,「你伤得重,得养些日子。」
我看着那人眉头挑了一下,低头,以拳抵唇,咳嗽了一声。
我忙不迭关好门窗。
他身子骨很好,恢复得很快。
那么重的伤,竟只过几日就能下地了。
季伯把家里唯一一
件厚棉袍给他穿,他穿着短了一截,显得有些滑稽。
腊月二十三,我搭了许家的牛车赶集。
周绥安神色动了动,和季伯说他也去。
许家阿妹藏不住事儿,平白瞅了周绥安好几眼。
她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悄悄问我,「来之姐,你们家还有这般亲戚?」
我说不是,他只是我捡回来的。
阿妹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道,「这样的人儿也能捡到?」
是啊,这样矜贵的人儿。
偷偷往后看一眼,他在假寐。身坐牛车,也仿佛坐在镶金嵌玉的轿辇,眉宇间清贵疏离。
仿佛察觉到目光,他睁开眼,正巧撞进我一眨不眨的眼里。
我慌张地挪开脸,脸发烫,羞得耳根子都红了。
身后似乎有一声极低极浅的轻笑。
我在集市买红纸,买祭灶的糖瓜,再给季伯买一点止咳的雪梨浆。
周绥安跟在我身后,只在路过书店时,驻足片刻。
我咬咬牙,将准备给自己买新头花的钱掏出来,拽着周绥安进店里。
店里挂了一幅很大的字。
我看不懂,但周绥安盯着看。
我想,那应当是很好很好的字。
后来我才知道,那幅字写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
我们买了笔墨纸砚,但笔是茅笔,墨是灶墨,纸是粗麻纸。
我即使清空了荷包,也依然配不上周绥安。
回去的时候,牛车颠簸,他坐在我对面。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影绰绰,和我的影子融在一起。
他撑着头,望着远山,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趴在炕沿上,看周绥安写字。
他写字时背挺得很直,眉目低垂,睫毛投下浅浅的影。
原来再骄矜的人儿,在写字时也是这般乖顺。
他手腕悬着,我就下了炕跑去他身边看。
我不识字,却感觉在粗麻纸上晕开的墨团好看极了。
「在看什么?」他没抬头。
「看你写字。」我老实回答,「比季伯贴的画儿还好看。」
「想学么?」
我忙摇头,后退了几步,「我笨,学不会。」
「不试试怎么知道?」他抬头,冲我招手,「过来试试。」
我走过去,他重新铺了张纸,将笔塞进我手里。他手指纤长,骨节分明。
我的手虽不粗短,但满是老茧。握着那杆笔,别扭极了。
他复上我的手,带着我落笔,「写你的名字。」
季字在我手下抖成了波浪,我急得鼻尖冒汗。他却极有耐心,一遍遍带着我写。
可他一松手,那些笔画便又散了架。
我急得快哭了,「我不行…别浪费钱…」
他俯下身来,和我平视,「那要试试写我的名字吗?」
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跳了一下,我点点头。
他重新铺开一张纸。
「周绥安」三个字跃然纸上。
「绥者,安也。」他说,复又盯着我,试探性地唤了一句,「安之?」
我的心脏怦怦跳,快得要跳出胸口。
除了季伯,再无人叫我安之。
周绥安的名字似乎更难写,比我的难多了。
我们练了一整个下午,我嫌废纸,就拿了树枝子在门口的土地上写。
他也由着我,蹲在我旁边,带着我一遍遍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