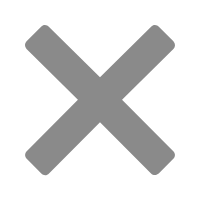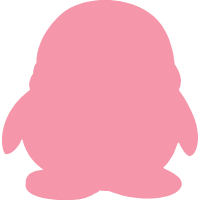-
泾河春雪
本书由果悦文化_好看的言情小说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腊月初八,我在山上捡到个漂亮公子。
后来,国公府的马车接走了他,宰相千金是良配。
而我南下,用他给的酬谢开了间茶馆。
又一年上元节,他循着茶香进茶馆。
我笑着欢迎,转身扇火时,衣领滑出一截红绳——是我从小到大的贴身玉佩。
那瞬间,他脸色骤变,血色褪尽,颤着声问我:
「这玉佩,你从何而来?」
1.
腊月初八,大风,刀子似的刮得人脸生疼。
我顶着积雪往山上走,要去采最后一茬冬茶——泾河春——卖了钱好给季伯买药。
镇里的大夫说,咳疾是富贵病,要用药一直养着。
我是季伯在泾河边捡到的,可能冻坏了脑子,我做事总比旁人慢半拍。
许家阿妹教我识字,十个字我能忘九个。
但我从小就鼻子灵,能闻香辨茶。
季伯总会自豪地看着我,说安之将来是有大造化的人。
我叫季来之,但季伯总叫我安之。
他不识字,想了好久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希望我安之安之。
所以,我是先闻到他的——风里刮来血腥气,还带着一丝极淡的沉香香气。
我放下篮子,顺着味道往里走,至一处洞口。
我拨开洞口遮掩的藤蔓,一眼就看见了他。
他躺在那儿,黑色大氅拖在地上,脸色白得像纸,嘴唇泛青,眉头紧锁,鼻息微弱。
我使出全身力气将他从洞里拖出来。
他很沉,我将他拖进背篓里。
又将采好的泾河春小心翼翼包起来放进怀里,一步一步往山下挪。
到家时,月亮都出来了。
季伯撑着病体在屋外焦急徘徊,见我带了个人回来,吓了一跳。
「安之,这是……?」
「我捡的。」我喘着粗气说,「就像您捡我一样。」
我们将那人安置在炕上。季伯烧好了水,我翻出压箱底的干净布,替他擦洗了伤口。
他伤在左肩,深可见骨。
身上料子摸起来柔软顺滑,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的料子,在油灯下泛着浅浅的光。
季伯又拿出仅剩的金疮药,拄着拐去村西头敲门,急匆匆带回来个村医。
趁着村医上药,季伯在屋外低声同我说。
「这人来头不小,咱们这小村子,怕是留不住。」
我没吭声,垂着头,借着月光将采回来的茶一一分好。
夜里那人发起高烧,浑身滚烫。我只能拧了帕子敷在他额头,一遍遍地换。
窗外北风呼啸,屋内油灯如豆。
我坐在炕边的小凳上,看着他的脸。
眉目如画。
这样贵气的人儿,怎么会浑身是血地出现在我们这荒郊野岭?
我端了药进屋。
他醒了,见有人来,他迷蒙的眼神瞬间锐利、清明。
「你是谁?」他声音喑哑,带着久居上位的质问。
我把药碗放在炕沿,答他:「我叫季来之。上山采茶时见你昏迷,将你背回来的。」
他起身时牵动伤口,闷哼一声。我上前扶他,他侧身避过,手悬在半空。
我缩回手,指着破瓷碗:「该喝药了。」
他盯着黑糊糊的药汁,没动,旋即看向我:「这是何处?」
「泾河村。」我说,「离镇上二十里。」
季伯听见声响,拄着拐进门,见他醒了,松了口气。
「公子可算醒了,我家丫头守了你几夜呢。」
他神色稍缓,向我道谢,礼节周到,客气疏离。
「在下周绥安,姑娘救命之恩,周某定当重谢。」
周绥安——
名字在我舌尖上打了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