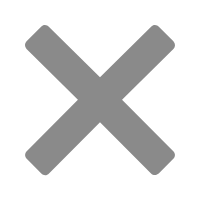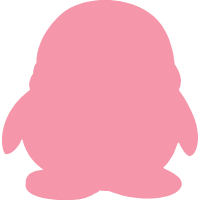2
照顾一个癌症晚期的老人,和照顾一个孩子,完全是两个概念。
前者,是在和死神抢时间,是在和人性的尊严做早已注定失败的斗争。
顾言舟留下的抚恤金,在昂贵的靶向药和ICU费用面前,就像投进火炉的雪花,瞬间蒸发。
为了维持这个家,为了给婆婆续命,我白天在设计院拼命画图,晚上去接私活做翻译,周末还要去给高考生做辅导。
但我最怕的,不是累,而是回家。
推开门,迎接我的永远是一股混合着消毒水、中药味和老人排泄物发酵后的腐臭味。
“林宛!你怎么才回来!你想饿死我吗?”
婆婆的声音刺耳,自从顾言舟走后,她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暴躁。
仿佛要把丧子之痛全部转化为对我的折磨。
我放下包,顾不上喝一口水,赶紧去给她换纸尿裤。
那是一场噩梦。
那一团黄褐色的秽物沾满了床单,由于她剧烈地挣扎,甚至蹭到了我的袖口上。
我强忍着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还要温声细语地哄着她:“妈,您别乱动,我这就给您擦干净。”
“你是不是嫌弃我?啊?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早点死?你要是嫌弃我就滚!”
婆婆一把推开我的手,沾着秽物的手指狠狠戳在我的脑门上。
“如果你照顾好言舟,如果你拦着他不让他去那个什么鬼基地,他怎么会死?都是你!你是扫把星!你克死了我儿子!”
这一刻,委屈像决堤的洪水,几乎冲垮我的理智。
我想大吼,我想把手里的脏尿布甩在她脸上,我想告诉她,我也失去了丈夫,我也在为了这个家拼命!
可是,看着床头柜上顾言舟的那张黑白照片,看着他温润如玉的笑脸,我忍住了。
“妈,我没有嫌弃您,言舟不在了,我会替他尽孝。”
我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像是自我催眠。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三年。
为了给顾念凑学费,我卖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
为了给婆婆买止痛药,我停掉了自己的社保,甚至在发高烧的时候为了省钱不去医院,硬扛着在家里还要给全家人做饭。
我的手变得粗糙不堪,脸上长出了色斑,才二十八岁的我,看起来像四十岁。
深夜,当婆婆终于在吗啡的作用下睡去,顾念也做完了作业入睡。
我一个人坐在阳台冰冷的地板上,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手里握着手机。
我想给顾言舟发微信,想告诉他我好累,真的好累。
但我知道,那个头像再也不会亮起。
有时候,一种可怕的念头会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海。
如果顾言舟没死该多好?哪怕他残废了,哪怕他躺在床上不能动,至少还有个人能听我说说话。
又或者,如果我也死了呢?是不是就解脱了?
“嫂子……”
身后传来怯生生的声音。顾念穿着不合身的旧睡衣站在身后,那是顾言舟以前的T恤改的。
“嫂子,妈又吐了。”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将眼泪逼回去,撑着麻木的双腿站起来。
“来了。”
这就是我的生活,没有尽头,只有日复一日的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