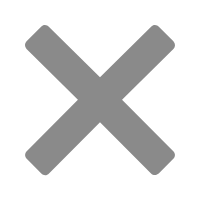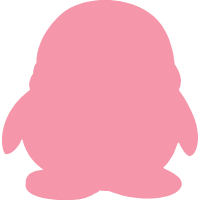3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他一次都没来。
只有宋媛发来短信:“景逸陪小杰去海洋馆了。姐姐好好休息,别总用生病绑着男人。”
我把手机扔进垃圾桶。
又捡回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回复:“宋媛,你会遭报应的。”
她秒回:“那姐姐要活得够久才行哦。”
后来我才知道,顾母对宋媛的偏爱,根植于骨子里的门第观念。
宋家虽然败落,但宋媛是在顾母眼皮底下长大的。
她熟悉豪门规矩,懂得如何侍奉公婆,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些都是我这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永远学不会的。
而更重要的是,小杰是男孩。
在顾母那套陈腐的观念里,女儿是“外人”,孙子才是传承。
哪怕这个孙子可能血统存疑,但只要名义上是顾家的种,就能保住顾家在圈内的脸面。
至于我的孩子?
顾母私下对顾景逸说过:“温婉那种小门小户出来的,能生出什么好货色?要是女儿,趁早打掉,别浪费顾家的资源。”
中秋家宴设在顾家老宅。
我穿着宽松的旗袍,七个月的孕肚已经很明显。
顾母瞥了一眼:“尖肚子,肯定是女儿。”
宋媛掩嘴笑:“女儿好呀,贴心。”
她的儿子小杰满场疯跑,故意撞了我好几次。
我踉跄着扶住桌子,腹部传来一阵钝痛。
“怎么了?”顾景逸终于注意到我。
“没事…”我话音未落,身下一热。
羊水破了。
黄浊的液体顺着腿往下流,染透了浅色旗袍。
满桌宾客哗然,顾母脸色铁青:“丢人现眼!还不快扶下去!”
我被两个佣人架进客房。
阵痛来得又快又急,像有只手在腹腔里疯狂撕扯。
我抓着床单,指甲劈裂了也感觉不到疼。
“叫…叫医生…”我嘶声喊。
门外传来顾母冰冷的声音:“已经叫了,等着。”
可阵痛间隙,我听见她在走廊打电话:“…对,早产,才七个月…刘医生,您看要不要保大人?孩子估计也活不成…”
我浑身血液都凉了。
这时,小杰的哭嚎声炸响:“爸爸!我肚子疼!好疼啊!”
顾景逸焦急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怎么回事?”
宋媛带着哭腔:“不知道啊,突然就疼得打滚…景逸,快送医院吧!”
“可是温婉她…”
“妈在这儿看着呢!”顾母扬声说,“你先送孩子,女人生孩子没那么快!”
脚步声犹豫了一瞬。
然后渐行渐远。
我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有眼泪疯狂地流,混着冷汗浸湿枕头。
凌晨两点,我在剧烈的宫缩中感觉到孩子往下坠。
没有医生,没有护士,只有一个老佣人颤抖着说:“太太…我看到头了…您、您用力啊!”
我咬破了下唇,血腥味弥漫。
最后一次用力时,我听见了自己骨头碎裂般的声音。
然后是一声微弱得像猫叫的啼哭。
“是女孩…”老佣人哭着把孩子递到我眼前。
那么小,浑身青紫,但胸口在微弱起伏。
我挣扎着用旗袍内衬裹住她,体温传递过去的瞬间,婴儿的哭声稍微大了些。
她还活着。
门外突然传来宋媛的声音:“医生来了!快看看孩子!”
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冲进来,粗暴地扒开襁褓。
他听了听心音,摇头:“没气了。”
“不…她刚刚还在哭…”我嘶声说。
男人没理我,转身对门外的顾母说:“节哀,早产儿脏器没发育完全。”
顾母叹了口气:“也好,少受罪。”
他们全都走了。
房间里只剩我和怀里渐渐冰凉的小身体。
不…不对…我颤抖着把手贴在她鼻下。
还有呼吸。
微弱得几乎察觉不到,但她还在呼吸!
我猛地环顾四周,抓起梳妆台上的剪刀,剪断脐带。
然后撕下床单裹紧孩子,踉跄着下床。
经过梳妆台时,我看到镜子里的人:披头散发,满脸血污,眼睛红得像厉鬼。
我抓起眉笔,在撕下的旗袍内衬上写:
“顾景逸,你的女儿死了。如你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