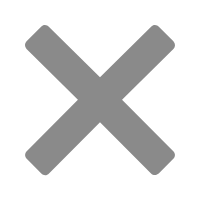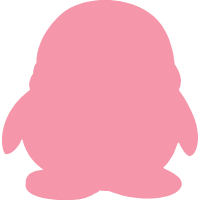2
我握着判官的笔,蘸着那点幽蓝的火光,重重地落在了沈惟川的名下。
「不必给我,」我抬头看他,「这妖骨,给我夫君就好。」
判官握着伞柄的手微微一顿,似乎有些惊讶。
「他不是说女人天生就该以色侍人?那便让他替天下女子,当一次玩物。」
判官沉默了片刻,忽然低笑起来。
「你不怕将来后悔?」
我擦掉嘴角的血迹:「我只怕他不够惨。」
判官收起册子,黑伞一转,身形慢慢变淡。
「如你所愿。」
「七日后,便能看见效果了。」
妖骨入体的第七天,沈惟川一大早就发了火。
他嫌官袍料子扎人,嫌熏香味道刺鼻,一早上砸了两个茶杯。
我跪在一旁收拾碎片,他烦躁地踱步,吼我:「滚远点!你身上的脂粉味熏得我头疼!」
我垂下眼。
我今天根本没有熏香。
他只是在烦躁,烦躁自己身上那股子怎么洗都洗不掉的若有似无的「香气」。
那不是花香,也不是脂粉香,倒像是……新晒过的被子,混着一点点刚剥开的橘皮味。
清爽,干净,让人忍不住想靠近。
他在礼部当值,回来时脸色更难看了。
「见鬼了,」他扯着领口,一脸厌恶,「那些同僚今天都怎么了?一个个往我跟前凑!」
他灌下一大口凉茶:「连吏部的张尚书,那个老东西,今天居然拍了我两次肩膀,说我……说我闻着挺舒心!」
他恶心得直反胃。
我低着头,假装什么也没听懂,上前替他更衣。
我故作温顺地说:「夫君许是累了。您最近清减不少,身上……」
我顿了顿:「身上香得像新晒过的被子,很好闻。」
他猛地瞪向我!
我“吓”得往后一缩,怯生生地说:「妾身……妾身只是实话实说。」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大概是觉得我这个被他踩在脚底的蠢女人也玩不出什么花样,终于还是把火气压了下去。
「一身汗味,好闻什么!」他厌恶地甩开袖子,「备水!我要沐浴!」
他一晚上洗了三次澡,换了三套衣服,差点把皮都搓掉一层。
可那股「肌骨生香」还是牢牢地长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无意间在他面前提起。
「夫君,过几日便是上元花宴,京中贵人云集,您也可去散散心。」
他本就烦躁,听我这么说,更是皱眉。
他一向看不起那些宴饮,觉得是浪费时间。
我继续劝:「您近来清减,气色不好。若在宴会上露个面,也好叫同僚们宽心。您这样……倒显得有些孤僻了。」
「孤僻」两个字刺中了他。
他最是在意自己「清贵端方」的名声。
他冷哼一声:「多事。」
但他终究是听进去了。
我看着他烦躁地摔门而去,知道他一定会去。
沈惟川,你不是最喜欢「应酬」吗?
我只是把你往你最喜欢的名利场里,再推一把而已。
上元花宴,设在曲江池畔,是京城最大的名利场。
赴宴前,我贴心地为他准备了衣袍。
一件月白色的广袖长衫,领口袖口用银线绣了暗纹,衬得他那张本就出众的脸,更是清俊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