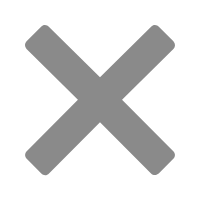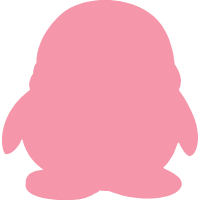4
她许是看出我心中的困惑,又或者想要我死个明白。
皇后屏蔽了四周,让我凑上前来。
「凭什么你们能嫁给自己如意郎君,而我只能守着这死气沉沉的后宫。」
我浑身颤抖,说不出一个字。
难怪,难怪。
那些被拆散的有情人,皆因为这中宫之主的嫉妒。
豆蔻年华却嫁给了四十多岁的老皇帝。
每每看到那些跟她曾经一样年纪的女子,许配的夫家,无一不是相貌姣好的男儿。
崔瑾后仰着靠在椅背上,欣赏着我的绝望:「本宫瞧着,昌平公主活泼可人,与陆世子年岁相当,正是良配,这救了一对怨侣,又成全一对佳人,岂不是美事一桩?」
原来如此。
原来她早就计划好了。
从她问陆嘉学婚期的那一刻起,或许更早,她就盯上了我们。
什么拯救怨侣,不过是她满足自己扭曲掌控欲的借口。
可我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介臣女,砧板上的鱼肉。
就算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
天亮时,一顶灰轿悄无声息地离了宫。
父母即使猜到真相,也只能打碎了牙,咽下了这份苦。
后来我听偷偷来看我的丫鬟哽咽着说,陆世子脸上并无多少喜色,但也未见多少抗拒,沉默迎着轿子,拜堂,行礼,送入洞房。
等到第二天一早,才发现躺在床上的是昌平公主。
可木已成舟。
甚至他还要随着公主,叫崔瑾一声母后。
在中云寺的日子,是望不到头的灰暗。
崔瑾为了督促我,日日夜夜找婆子过来规训。
我不止一次想过死,可想到父母,他们或许还在为我奔波,又忍了下来。
至于陆嘉学,他从未打听过我在哪。
母亲偷偷来看过我几次,每次都以泪洗面,短短数月便苍老了十岁。
她告诉我,父亲为了救我出来,在赈灾中被流民殴打,气急攻心,没撑过夏天就走了。
临终前还握着我的手帕,叫我的小名。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了,娇娇能出来奔丧,带上盘缠,龟缩着,别让崔瑾发现。」
尚书府的门挺,就这样衰落下去。
我逐渐麻木。
痛到极致,反而没那么痛,我写给陆嘉学的每一封求救信,都被人拦截了下来。
我回京那日,崔瑾仿佛忘了我这号人,也许是觉得我彻底废了,造不成威胁,母亲散尽家财,为我开了一个胭脂铺,她的身体在日积月累中已逐渐不太好了。
我顶着短短一茬的头发,和她抱头痛哭。
活下去,成了最实际的问题。
我不再用以前的名字,街坊邻居只知道新来的老板娘姓宋,沉默寡言,手艺却不错。
调的胭脂颜色好,价格也公道。
日子清苦,但能守着母亲,靠自己的双手挣一口饭吃,我已不敢再奢求更多。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听着母亲压抑的咳嗽声,看着镜中自己那张郁色的脸,还是会恍惚。
原来,已经是第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