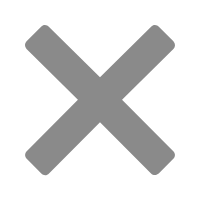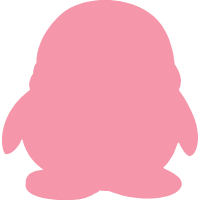4
吃醉酒失足落水,本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能算他时运不济。
更何况,傅怀瑾隔三差五不是诗会应酬,便是与婉娘“月下吟诗”,我难道还能成日盯着他、管着他喝不喝酒?
我拿起帕子,拭了拭眼角,“都是我不好,留不住夫君的心,也留不住他的人。是我没拦着他出去吃酒,才害他夜不归宿,掉进池里。”
一位傅家族老适时出面,唱起了白脸:“侄媳妇,这话重了。怀瑾命数如此,怨不得你。”
一屋子人,红脸白脸,唱的都是一台戏。
傅怀瑾本是无根浮萍。
自从被父亲收为义子,他便再未动过离开的念头。
当年父亲要为他另择良配,是他自己跪求,非我不娶。
这帮亲族也硬是靠着沈家,在京城立起了“傅氏”的门户。
后来,我父兄葬身火海,母亲心死遁入空门。
沈府,也就此成了傅府。
他安然享受着沈家留下的一切,不清不楚地在府外养着婉娘时,这群亲族没人一个人说这样不妥。
如今傅怀瑾死了,留下这偌大家业,他们便理所当然地觉着,自己该分上一杯羹。
我冷眼看着他们在我面前做戏,只吩咐下人按礼制操办丧仪。
本想装装样子,再破财打发走这些苍蝇,顺便集点傅怀瑾的心碎值。
不料那傅姨母突然一抹脸,露出一副破釜沉舟的决绝:
“有件事,我憋了多年!今日,我必须说出来,为瑾儿、为傅家主持这个公道!”
一股不好的预感爬上脊背。
我出声打断:“姨母,我如今是傅府当家主母,府中事务,不劳您越俎代庖。”
“你闭嘴!”她厉声道,“谁是你姨母!瑾儿,他是我亲生的骨肉!”
她抖出一张契书,“当年我妹妹无子,从我这儿过继了瑾儿,族老们都是见证!”
“我本不想认,如今实在不放心你一个弱女子当家,才站出来!”
我笑了,“姨母既说夫君早被过继,与您已非母子,现在又何须为我这寡妇劳神?”
“姨母没资格,那我呢?”
我循声望去,傅怀瑾的青梅,终于来了。
婉娘被丫鬟搀着踏入灵堂,双眼红肿,似是哭了一路。
她站到我面前,如同面对宿敌:“我已有了怀瑾的骨肉!若我没猜错,他早拟好了休书要休弃你!”
我纳闷傅怀瑾这死鬼怎么还不出来,闹了一上午心碎值迟迟没动静。
索性开口激她:“我与夫君夫妻八载,举案齐眉,你休要在他身后污他清誉!”
话音刚落,那迟迟不现的魂魄终于飘了出来。
傅怀瑾湿漉漉地立在婉娘身侧,面色铁青地看着我。
系统操作下他被池水泡了一夜,导致尸体已经有点泡发了。
现在这副肿胀的尊容看起来狼狈又可笑。
婉娘只当我仍被蒙在鼓里,冷笑道:“亏你还是官家小姐,竟愚昧至此!怀瑾早已厌弃了你,休书就在他书房暗格里呢!”
傅家人骚动起来,傅姨母已迫不及待:“去书房!现在就去!让这毒妇心服口服!”
书房前,一众傅家人和吊唁的宾客,等着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