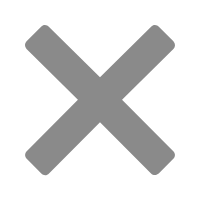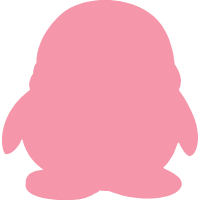4
他眼底的恨,和六年前逼我签字结婚时,一模一样。
为了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我在危险的哀牢山写生,
江衍突然出现,
神志不清,
他紧紧的把我按在尚未着色的画上,
血腥味混着花的异香,
身下的彼岸花,
颜料混着血水流进草里。
我拼着最后一丝力气把江衍藏好,
引开了埋伏的追兵。
可第二天,报纸上登着:
林瑶瑶凭《永不凋谢的彼岸花》封神,
画中血色花海,
据说能勾人魂魄。
她用我的画,成了华国第一女画家。
一盆水泼醒了昏倒的王奶奶,
我瞳孔骤然微缩:
“不要”
江衍正把安安往浴室拖。
“最后问一次,林微在哪?”
王奶奶扑过去抱住他的腿,
被他反手推开撞在墙上:
“她死了!我再说一遍她死了!”
江衍笑了,他拎着安安的后领,
像扔小猫似的把她扔进浴缸,
哗哗的冷水瞬间漫过孩子的腰。
“找不到她,就用她的种抵债。”
他拿出那把牛排刀,刀刃渗出惨白的光,
“听说钝刀子剌人最疼”
“一片肉,我等她一刻钟。”
刀尖刚碰到安安的胳膊,
我就疯了似的冲过去,
魂体撞在他身上,
却只让他肩头颤了颤。
“别碰她!”
我嘶吼着去夺刀,
手指一次次穿过冰冷的金属,
什么都抓不住。
“妈妈……” 安安的哭声在空旷的浴室回荡,
血水已经染红了浴缸。
王奶奶连滚带爬扑到浴室门口,
被保镖死死按住,
她看着浴缸里的血沫,
嗓子喊得劈了叉:
“畜生!你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外面众人的咒骂声、安安的呜咽声、江衍的冷笑混在一起。
他的刀又落下去时,
王奶奶突然挣脱保镖,
抢过刀狠狠扎向他的手背。
“噗嗤” 一声,
血珠从他手背上涌出来,
滴进浴缸。
我眼睁睁看着那两缕血在水里慢慢靠近,
没有排斥,没有分离,
像两条久别重逢的红蛇,
悄无声息地缠在了一起。
江衍没注意这一幕,
他正甩着手骂 “疯婆子”。
“磨磨蹭蹭的。”
他冲门外喊,“张医生,进来。”
穿白大褂的男人提着医药箱走进来,
瞥见浴缸里的血,
推了推眼镜,从箱子里翻出麻醉剂。
“不用打。” 江衍踢了踢浴缸边缘,
“直接取,新鲜的才好用。”
安安只能发出细碎的呜咽,
小手在水里徒劳地划着。
我扑过去想捂住她的眼睛,
魂体却穿过她的小脸。
“按住她。” 张医生的声音比手术刀还冷。
江衍掐住安安后颈,迫使她仰起头。
冰凉的开睑器塞进眼眶时,
安安的身体猛地弓起,喉咙里野兽般的嘶鸣。
王奶奶在门外被保镖死死按住,
头撞在门板上 “咚咚” 响,
骂声早变成了泣血的哀嚎:
“天杀的啊……那是你亲生的啊……”
血顺着安安的脸颊往下淌,眼眶变成黑洞。
江衍嫌恶地松了手,
他没看那罐储存了安安眼珠的 “备用件”,
转身扯了纸巾擦手,
视线扫过浴缸时,
突然顿住。
他手背上的伤口还在渗血,
血珠滴进水里,
竟和安安的血缠成一团,
在水面上晕开一朵妖异的红。
他突然像被烫到似的后退两步,
“张医生!张医生!”
他扯着嗓子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把这野种的血抽一管!还有我的!现在就去做亲子鉴定!立刻!马上!”
浴缸里的安安,
小脸白得像纸,
嘴唇发乌,
可那缕相融的血还在慢慢晕开,
像朵诡异的彼岸花。
“不可能……” 他喃喃自语,
指尖抠进门框的木纹里,
“她怎么可能是我的种?当年娶她就是个交易,她是大着肚子嫁给我的……”
眼睛死死黏在那管鲜红的血样上,
直到张医生拿着样本匆匆离开,他才跌坐在地,
盯着浴缸里渐渐凝固的血水,反复念叨:
“一定是哪里错了…… 不可能是我的……”
我飘在他身后,
看着他眼底翻涌的恐慌,
突然觉得可笑。
此刻他极力否认的血脉,
终究要以最残忍的方式,
砸在他脸上。
从江衍开始喊着要做亲子鉴定开始,
林瑶瑶就慌了,
她让佣人搀扶她走到浴室门口,
“阿衍,阿衍”
无人回应,一片死寂。
直到张医生的回归打破了寂静,
“基因相似度 99.99%…… 确认亲子关系。”
那行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手一抖,报告单飘落在地。
“不可能……” 他喃喃着。
突然又疯了似的吼,
“林微呢?!她到底在哪?!”
吼完又转向张医生,
“快!把最好的设备都调来!救她!必须救活她!”
林瑶瑶声音轻飘飘的:
“阿衍,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说不定…… 姐姐早就知道孩子是你的,故意藏起来报复你呢?你看她把孩子养在那种地方,心思多深啊。”
江衍猛地转头看她,眼神里第一次有了审视。
他抓起外套就往外冲,
路过王奶奶时停下,
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她的墓…… 到底在哪?”
王奶奶啐了口带血的唾沫:
“后山老槐树下,你自己去看!看你怎么对得起她!”
越野车在山路上疯跑,
江衍一脚踹开槐树下的土堆,
铁锹下去,
触到的不是棺木,
是裹着尸体的草席。
他亲手扯开草席的瞬间,
胃里猛地翻江倒海……